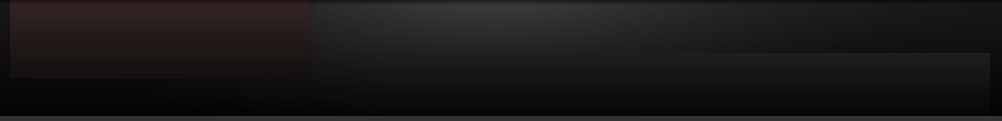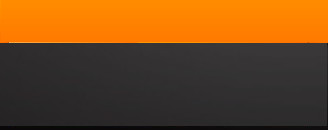首页、(万向注册)、首页2月14日,麻阳县石羊哨乡岩落寨村,向宏嘉和向永胜搭档跳了一段《正月贺喜正月天》,一旁伴奏的是向宏嘉的爷爷向宽牛,老人已是村里花灯的第13代传人。组图/记者陈韵骄
从湘西到湘南,再到湘北,几乎绕着湖南跑了一个大圈。正月十五已过,所幸三地的花灯戏都还未全然落幕。虽然每一地都相隔遥远,可它们的眉眼却依稀相似,你大可想象最早的流传是如何影响,而最终又因风土、语言、习俗甚或人口的流动迁徙,而渐生差异。
花灯起初都没有女性上台扮演角色,这种“南方二人转”的表演,眉眼和手势里有太多撩逗传情,于是只能由小子们乔装打扮一番。
麻阳县的著名花灯艺人聂榜榜(已故)因为妆容美丽,每演花灯戏“灯姑娘”,都会招来不少小青年的爱慕。新中国成立后,当地县文工团特地请他来做艺术指导,不少花灯戏老演员曾得他亲授指点,在他们的印象中,聂榜榜就是一个特别清瘦的老人,但一上舞台就变得灵动异常。
我们在麻阳县高村镇大塘村和石羊哨乡岩落寨村观看的花灯戏,仍然是由十几岁的男孩子们分别扮演“灯姑娘”和“癞花子”,简单化个妆后,就上了场,在锣鼓击出的节奏中,配合着掌灯师帮唱的《十月采茶》花灯调,相互戏耍,舞蹈,极是诙谐有趣。这种古老的花灯歌舞,明嘉庆年间就有记载,“元宵前数日,城乡多剪纸为灯,像鸟兽鱼虾等状,令童子扮演采茶故事”,民间称之为“摆灯”、“哑子灯”。
大约在咸丰、同治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玩法“跳灯”,渐渐取代了歌者不舞,舞者不歌的摆灯。这是大势所趋,因为常德的汉戏班子、辰溪的辰河高腔班子顺着水路来到了麻阳县城锦和镇。他们也带来了完备的戏剧体系和新的审美。麻阳花灯深受影响,开始自唱自舞,他们甚至不限于春节,凡有重大的民俗节日和各种巫傩活动,都会参与,求雨、求子、驱虫、祛病……不断地改进歌舞形式,原来只有二十多首花灯调,一下子翻了十倍,旦和丑的步法、花扇的用法也都以特有的名词迅速固定下来,“花灯形象三百六,飞禽走兽鱼龙猴,日月风雷花草木,打好花灯不用愁”,麻阳花灯现在使用的舞蹈、唱腔词汇基本上都是当时流传下来的。
聂榜榜在民国初年就试着用阳戏的套路,和搭档张冒冒演了一出灯戏《癞蛤蟆拜年》,好评如潮,但仍不能完全称之为“戏”。直到1961年,麻阳县成立了花灯戏剧团,才算是正式开创了“歌、舞、剧”合一的花灯戏。
听过不少麻阳花灯调之后,深觉由歌舞入戏不容易,表演程式或可借鉴各大剧种,但唱腔的改编十分困难,因为灯调始终是民歌结构,简单,重复,四五句循环往复,戏曲化程度不高。一旦题材扩大,角色增多,唱腔势必也要有丰富的变化以对应不同人物的情感、性格。至今,麻阳花灯戏也没有形成能代表一个剧种的主要唱调,这是它与嘉禾、平江花灯戏最大的区别。
2月14日那天,离县城20公里左右的石羊哨乡岩落寨村很安静。它地势高拔,站在村委会门前,就能远眺淡蓝色的群山。黑的屋顶,浅黄的土墙,三三两两出现在坡上或某个山坳里。61岁的向宽明从一户村民家匆匆走出来,领着我们往小山上走。房屋依从着苗寨特有的建制,一幢幢顺势而上,间隙处铺着石板。但传统的吊脚楼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水儿砖混结构的新房子。
向宽明住了五十几年的老木屋夹杂在新房中,深褐色的板壁居然比贴了瓷砖的邻居外墙打眼。他门前的晒场上聚集了不少乡亲,还有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,人们嚷嚷着要男孩子们跳花灯。两个十几岁的少年果然落落大方地站了出来,两人都有着青春期特有的瘦薄身材,瞳仁漆黑。脸庞清秀的向宏嘉,手里擎了一把小旦用的水红花扇;向永胜面容粗犷些,自然就担起了丑角。他俩都在重庆念技校。
70岁的向宽牛是向宏嘉的爷爷,也是师父,花灯传到他这儿已经13代了。他从布兜里掏出一面铜锣,嘡嘡嘡敲了几下,算是开了场。小哥俩随着锣鼓点子,跳将起来,周围的人唱着《正月贺喜正月天》,给他俩伴唱。
我没料到他们会跳得这么好。向宏嘉抿着嘴,嘴角挂着笑意,时而把扇子展开覆在搭档头顶,边逗边退;时而又收起扇子,面带嗔怒,作势敲过来。翘起的兰花指优美地指点着,漾起一片小小的风情。向永胜屈着腿,如小猴似的团团转,动眉毛,飞眼神,脸上的表情换个不停,偶尔伸手去撩拨对方的头发、下颏,又带着故意。
等他们下了场,人们都鼓起了掌,另一对少年又上场了。13岁的向浩南大概是久没跳了,忘记了“套子”,步伐凌乱,总跟不上身边的搭档,如此一来,小脸绷得紧紧的,全是紧张。他的师父向保保(音)在一旁一边敲着小锣,一边大声叹气,时不时地批评几句。这下更糟了,浩南楞在原地,不知所措,向宽牛捺不住性子,手里抓着锣跳将过去,摆了一个马步,现身指导。向浩南却听不得师父的批评,眼泪汪汪地赌气跑了。向保保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沮丧。
小孩子演花灯是传统,所以孩子们扮灯姑娘还是癞花子都没有太多抵触,谁的气质更适合演哪个角色,师父说了算。要唱好花灯并不容易,据说三年才能出一对资质出众的旦与丑,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,这已经不是一个非得达成的目标了,如果不是师父们还在苦口婆心,他们会有更多玩乐的选择。
在更远的年代,花灯班挨家挨户进行表演,大多在晚上进行,提着花灯笼走街串巷,还有一个送帖人,专门下帖拜访,接帖的人家都会邀请他们到自家表演。如果这户人家不要求“开五方”,那么花灯班就只唱“采茶调”,从一月唱到十二月,每个月四句唱词。人家太多的话,便省略两句。如此,一直唱到正月十五,结束的那天晚上,大家在空地上或者田边燃起熊熊大火,烧掉今年的花灯,又一个个从火堆上跳过去,驱走“瘟神”。
村里有一棵古老的大树,占据了最高点,大家都叫它“杨秀牙”,已经长到足够让人顶礼膜拜的年纪。花灯班出门唱花灯,一定要来拜拜这棵树,谓之“参神”,如果忽略这个仪式,“那一定会背时,出门锣会打烂的!”有的村子不一定会参树神,而是会去“盘瓠庙”,请苗王保佑,以免去波折。
麻阳县花灯戏剧团团长张锦芳今年四十多岁了,说起早年学花灯的情景,不时叹一声:“太辛苦。”他父亲曾经也是一名花灯表演艺人,他六岁跟着父亲学戏,跟着剧团演出,实在是不舍得离开。演丑角尤其累,每天练习各种步子,“刮韭菜”(扫腿)不知要刮多少次,“有一个‘鸡公倒立’,灯姑娘前面引,癞花子倒立着两手撑地走出来,腿还不能伸直,没点体力奈何不了”。现在这个动作基本上不用了,一则团里人少,二则着实费力气。
旦角常用扇子,舞台用法有20多个,引扇、推扇、照扇、飞扇……这些扇法又组合成不同的套子,雪花盖顶、鳊鱼上滩、飞蛾扑灯……一百多个套子娴熟运用,才能在台上自如。
团里退休的老演员瞿腊英踩着一双细高跟鞋翩然闪进来,橙色的围巾,变成时尚“奶奶灰”的头发,挽着精致的发髻,完全想不到她已经70岁了。她在排练厅示范了一个麻阳花灯戏的代表动作“老母猪拱苕”,很认真地告诉我:“这个动作的要领,在于身体猛然向前一倾。”幅度之大,真担心她会闪了腰。她却摆摆手,又唰地一抬腿,来了个“朝天蹬”,一条腿踩着细高跟稳稳立在原地,像棵树似的立着。我后来翻看剧团一本老相册时,看到了她上世纪七十年代扮演的老旦黑白照片,嘴角一颗媒婆痣,斜睨着眼,一脸轻蔑,和眼前这个讲话轻柔的老太太判若两人。她笑了笑:“我其实是演小旦的,当时需要演老旦,那也得演啊。”
我在相册中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物什的照片,像个头环,却又有类似弹簧的细竹丝。
“太极图!”他们抢着回答,张锦华又补充了一句:“现在没人会做了,差不多失传了。”
通过他们的描述,我才慢慢想象出“太极图”这个小道具的用法。这是专属丑角的配置,戴在头上,一个小圆凹槽正贴在眉心,一截柔软的细竹丝盘绕在其中,顶端附着一只小红绒球。丑角为了制造舞台效果,猛地一甩,绒球会从额头上弹出一尺来长,晃晃悠悠,不需要时,只一拍,它又能缩回去,紧贴在额上。传统戏《拉郎配》中要用到它。可从前会做太极图的老手艺人基本都去世了,后来的手艺人依葫芦画瓢只能做个样子,细竹丝弹出来后怎么也无法缩回去。
剧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遭遇了危机。看戏的人越来越少,资金严重不足,不光太极图消失,连戏服都找不出几件像样的,更糟糕的是,不少台柱子受不了每月几百块钱的清贫,纷纷离职改行。今年,他们有望拿到一个优秀的剧本,但资金从何而来,没有人知道。
嘉禾县蓝天剧团的演员王华雄打开手机,给我看他这两年送戏下乡演出时拍的照片。
他竟然拍了那么多戏台!湘南人爱看戏,古戏台多且美,嘉禾亦不例外。很多古老的戏台静静立在村中,台上柱子依稀镌刻着对联,有的字迹已模糊。左右两边的“出将入相”都空着,似乎后台的演员们正整冠静待琴鼓再响,好演一出堂皇世事。从田心村的一副戏台对联能洞悉人们看戏的痴迷:
心中只想调,管它缺柴缺米,爱看柳莺莺晒鞋。戏中没有宏大叙事,只有细碎而又平常的喜乐悲伤,在民间,它们被反复上演,常演常新。
像《下洛阳》,长达四个小时,有的人能站着看完全本。“冒根藤”(剧中人物,丑角)一上场,用湘南官话一口气念出五十几句道白,嘴功了得,下面一片叫好。这正是嘉禾花灯戏的特色之一,有的道白长达一百多句,需要很好的记性与气口。老艺人常说:“旦角靠水(即装扮),丑角靠嘴。”又说:“花灯小生最难找,丑角旦角最讨好。”
丑角不仅要嘴功好记性好,“脸子功”也要好,脸部表情要夸张风趣,每一块肌肉动用自如,说动哪块就动哪块,眼睛滴溜有神,透出一股子挑逗劲儿。后颈插一把扇子,时不时取下挽出各种扇子花。矮子步是丑角最重要的基本功,双膝微并,上身挺直,怀里像抱娃娃似的。旦角中也有丑角,叫“摇旦”,承包了爱挑是非的媒婆、性格粗鲁凶狠的继母、擅长骂街的泼妇等角色。他们有特殊的身段,两手背叉腰,外八字,扭腰幅度极大,摇摇摆摆,手拿烟杆或蒲扇,骂人时拍屁股跺脚,手心敲手背,活脱脱一个厉害妇人形象。
嘉禾花灯戏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有一些游离于剧情之外的表演程式,比如“打加官”。旦角出场,先拜打鼓师傅,然后做出门亮相的姿态,推开大门,两边一望,开始挂画、放画、扯线,再开“加官门”,取出折叠好的“天官赐福”,亮给观众,另一个演员从台内拿出一张名单,名单上写着本地一些有名气的人物,道出姓名,旦角于是将“天官赐福”牌一一放下。这时,台下燃起鞭炮,被点了名的人家纷纷送上红包。这相当于一个讨吉利的互动环节,被点名的人家不会拒绝,反而觉得是个好彩头。
嘉禾是我喜欢的几个湖南地名之一。一棵漂亮的禾苗,大概是农耕时代对此地无上的赞美。这里自古“粮足,种桑织布手工业皆丰”,人们衣食无忧,自然心情愉悦,往往“民乐随之,大开农耕,田间起舞”(《桂阳郡志·俗乐之八》)。县城是那么小,城外的乡镇村庄又是那么紧密,最远的一个也不过开车一小时的路程,以戏为乐的交流可以想象是多么频繁。此地的花灯戏同样也经历了“对子调”——“二小戏”——“三小戏”的变化历程,直到出现各种职业花灯戏班社。以钟水河为界,河东的“大岭四季班”、“龙潭花灯班”,河西的“民顺四季班”等,都曾热情高涨地送戏下乡。
2月16日一早,蓝天剧团的《下洛阳〉就在老城禾仓堡街道的圩场上演了。这一天,恰逢赶集日,石板路被各种小摊子挤得满满当当。老戏台上,写着“财阜熏弦”的匾额下,老员外正要出远门,吩咐继室马氏照料好一双儿女银秀和金柯。所有的故事都将发生在这一对小姐弟身上。他们被贪财的马氏虐待,马氏又被爱赌的弟弟纠缠,干脆雇他杀掉小姐弟,可这个舅舅下不了手,放了他们一条生路。姐弟俩流落街头,却又幸得太白金星相助,最终找到父亲,回到家中。
这台大戏的角色之多令人瞠目。老妪、少女、乞丐、谋杀者、神仙、鬼魂……纷纷粉墨登场。它充满了宿命因果、善恶有报诸多中国式戏剧元素,也流泻着中国式的慈悲——整出戏中没有人真正死去,就连一切恶的始作俑者马氏,在面对归来的丈夫和继子女时,也没有像欧洲童话《白雪公主》中的继母,被赐一双烧红的铁鞋。她的丈夫在女儿的恳求下,只说:“我给你干柴一把,糙米一升,你自去柴房磨灭你的性情,哪天改好了,夫妻自有团圆之时。”
剧中,银秀和金柯没有回家的盘缠,只能街边声泪俱下地乞讨,胡琴奏出凄凉的调子,两人一边哭诉身世,一边恳求众人帮助。放眼望去,台下许多老人早已两眼含泪,不时抬手拭去。姐弟越唱越伤心,高潮骤起,台前的人开始往台上扔纸币,后面的人也挤过人群来打赏,一时间,纸币纷纷落下,10元、50元、100元……人们仿佛融进了这戏里。我后来才知道,在嘉禾,这一段有名的催人泪下的“哭板”差不多已经取代了惯用的哀乐,凡能在乡间听到,必定是某家在办丧事。而“打彩”(打赏)的传统也由来已久,甚至会在演出中不时燃放鞭炮以示喝彩。
剧团的音乐指导、嘉禾县文化馆前馆长李正亮告诉我,像“哭板”在嘉禾花灯戏中属于正调,意即专用曲调和通用曲调,它是花灯戏曲化后形成的唱腔。载歌载舞的花灯小调也能任意用在戏中,适于卖场、戏耍的情节。还有一种路调,是对子调向花灯戏过渡的一种唱腔,出场、走场、行路时常常用到。
小乐队也吸引了我。看上去认识的,实际上会叫错名字。比如说那个长得很像二胡的,肯定不是二胡,而叫翁琴(也有写成瓮琴)。原来都是艺人自制,琴筒比二胡大,琴轴也比二胡粗,筒口成喇叭形。小锣是本地铜匠所制,形如碗,锣心凸出,亦叫碗锣、顶顶锣。各地花灯戏中常用到小钹,又叫扬钞,钞叶很薄,发音清爽,欢快的乐曲中加入小钞,节奏更明快,但如果掌握不好,那就破坏力惊人,所以他们常说:“打得好就是钞子,打不好就会吵死。”
旧时的花灯乐队,一般由四五人组成,且每人都能兼奏两种以上的乐器,奏翁琴的必得兼唢呐,司鼓的兼小钞,大锣兼大钹,小锣兼检场。乐手们的座序也有讲究。一般会在舞台中央后部放一张四方桌,鼓在右,称武场;唢呐、瓮琴等在左,称文场;大锣大钹坐中间,称中场。
我跑到后台,几个演员正候场,写着唱词的剧本扔在一口大箱子上。演乞丐的剧团团长雷衍奎穿着一身补丁服,手拿竹棍,准备上场。他觉得脸上妆太淡,不像叫花子,干脆在地上抹了两把灰擦在脸上。在传统戏里,这个形象是全身披草,头戴草帽,腰间系着一条草裙,如同一个“草人”。我喜欢听他唱叫花子专用的“神仙调”,云板敲出清脆的节奏,竹棍亦随节奏的的笃笃击着地面,念白一句句朗朗上口。
42岁的王华雄只要一下场就捧着剧本练台词,他一会儿演马氏的好赌弟弟,一会儿又扮客店小二。他是这个民间剧团年轻的演员之一。平时,他是某电器产品的营销经理,演戏是他最大的热爱。他还记得,1986年,他念初一,在县城看了一场《十月小阳春》,那是他印象中最后一次看花灯戏,此后再也没演过。县里没有官方剧团,民间剧团重新拾起花灯戏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。成员大多是业余爱好者,年纪偏大,像蓝天剧团,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,专演老生。爱看戏的群众也是老年人居多,八零后九零后几乎对此无感。
龙潭也是个自古爱唱花灯戏的地方,当年,此地的祁剧、龙灯亦很出名。现在村里的剧团也能演十几出戏。村里的大戏台上,11岁的胡玲、胡伊蕾两个小姐妹正一个挽扇子,一个转手帕,跳得热力四射,阳光把她们的身影镀了一层浅浅的金色,红扑扑的脸蛋儿和黑眼睛好看极了。她们俩都是小戏迷,喜欢花灯戏,强烈要求学,所以才跳得这么来劲。
一个外地人在平江看花灯戏,若无字幕辅助,是听不懂几句的。偏偏最逗趣的“三花”(丑角)总是有大段大段的念白,他一开口,当地人的笑声就如潮水一波波涌来,而你只能尴尬呆望。
在语言学家听来,平江话肯定是最古老的汉语言,属于湖南赣语的一支,十里三音,光声母就有22个,韵母更多,62个,县城话算是最好懂的。
花灯戏的唱腔声调自然也跟着宛转起来,高低起伏,音程关系复杂。小旦小生常常平静念出一句道白,句末却蓦地拖出一声高锐的假嗓,初听时不免惊住了。不过,其唱腔仍以中平音为主,很少高腔,而且它很早就形成了自己正调——川调和打锣腔。它的灯戏调特别丰富,一出戏里几乎每个人物都有专属的调子,谢师有谢师调,过江有过江调,连王婆骂鸡也有骂鸡调;“反西湖”用来表现忧伤情绪,“颠花轿”则喜气洋洋。
传统的平江花灯戏行当体制,开始称为“三个半”柱头,生、旦、丑三个,半个是“点余相”。何谓“点余相”?其实是个介于生、丑之间的特殊角色,他表演时帽子齐眉戴,戏不多,场场要,故称为半个柱头。
小丑一般穿对襟短袖便衣、彩裤,脚穿布鞋或草鞋,脸上两腮一点红,红中一点白,倒八字眉,花鼻子,头上包巾或戴草帽,道具是一把扇子,小旦则是扇子加手巾。平江演灯戏一定会有四盏、六盏、八盏灯,旦、丑在灯下做戏。小丑不但要能说,还得练特殊的“口功”,比如说荷叶口、梭口、直一字口、鲜鱼嘴……我很想在平江找一个三花艺人露一露,可惜,这种传统功夫在民间都只剩下皮毛了。
三墩戴市花灯剧团有五十多年历史了,第一届花灯戏大赛也在这里举办。我们到达的时候,村里的花灯戏班子刚从外地表演归来,他们还兼舞龙灯,村里一支妇女龙灯队小有名气。此时,演员们穿着舞龙的表演服围坐着一户人家厅堂里烤火,几位老艺人坐在另一边。
“龙游沧海,凤啼山……”一位老者起身开腔唱了起来。咳嗽一声,继续念白:“头戴胭脂帽,身穿四海青。打扮军家样,眠民该不知……”
平江县文化馆副馆长肖平饶有趣味地听着地道的平江花灯戏唱腔,告诉我,这是传统剧《正德戏凤》,从花鼓戏套用过来的。主角是明代正德皇帝,他上场亮相,头一句是引子,然后是念白,念白完了之后,要在椅子上坐下,接着唱整出戏的背景。所有的花灯戏都是如此架构。
旧时,平江灯戏演出条件粗陋,除通用一般道具外,剧中所需标志性和装饰性道具,主要是扇子、草帽、手帕为主,舞台搭在草坪、沙洲或堂屋家神牌位下,用几条长凳或箱桶做底,铺上门板或木板即成。照明用的是桐油灯,甚至是松明火。装扮也简单,不甚讲究,小旦穿窄袖彩衣扎腰带,下着彩裤或裙,脚穿布鞋,头上梳头插花,水粉扑脸;小丑一般穿对襟短袖便衣、彩裤,脚穿布鞋或草鞋,脸上两腮一点红,红中一点白,倒八字眉,花鼻子,头上包巾或戴草帽,道具是一把扇子,小旦扇子加手巾,流传至今。
平江灯戏亦从民间而生,同时借鉴了京剧、花鼓戏、巴陵戏等戏种的表演特色,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比如,它把渔鼓、莲花闹、送春牛、赞土地这些说唱表演,都糅合进去,以唱为主,加上道白和表演动作,舞蹈动作又吸收了民间大量狮舞、龙舞、巫舞及彩龙船、扎故事等等,热闹异常。
肖平起身给我演示“坐下来”的表演动作,“念白完了后,转身走向椅子,但是不能马上坐下,这叫‘滚簟筒’,是不允许的。必须转过去后,再回转一下,然后落座。”
开门动作也有讲究,行话叫“阴阳手”,两手上下,模拟打开门闩后,必后退一步,关门则要往前一步,这才符合生活常识规范。他指着一段花灯戏视频说:“你看,这个演员就是平平推开,忘了后退。”
当地把丑角叫作“三花”。三花的表演分量最重。传统剧目《林三守花》中,可以窥见不少剧种的影子,他被两个采花女拉扯得前仰后合,步态动作形似牵线木偶,这是模仿了皮影戏;中间还有一段京胡独奏,借了巴陵戏的曲调。看来,一个成功的三花须得吹拉弹唱念做打,无一不精,才能在台上自由洒脱。
在三墩乡,几位民间艺人演奏了一段欢快的“开场锣”,我们的注意力全在其中一面小锣上。敲锣者童治安不时敲击一下,又将它迅速抛向半空,落在手中后再次敲击,抛出,既像是演奏,又如同杂耍。小锣离开手的束缚,没有了闷响,抛向半空时发出的声音分外清远响亮。这是平江花灯戏中最有特色的“抛天锣”,那面鬼灵精怪的小锣又叫云锣或啵锣。它和乐队使用的低音大锣形成16度的音差,十分悦耳。据说,旧时技艺高超的乐手,能两两对抛击打,令人眼花缭乱,而节奏一点不乱。如今,能玩这手绝活的艺人已经寥寥无几了。
三墩乡已故的老艺人杨荣昌,留下了一卷写在雪白竹绵纸上的“祭台辞”,工工整整的小楷,笔迹纤细,记录着祭祀文字和符箓。在平江,每一个戏班搭台演出时,必先祭台神。祭神仪式中,要杀掉一只大公鸡,将鸡头用红布包好,外面缠绕七色丝线,然后将红布包放进一只罐子里,埋在戏台后面的山上,鸡血洒向四周。班主登台请神,演武将的演员则拿起鞭子四方抽打,班主点上香烛纸钱念诵祭辞。这与麻阳花灯班出门“参神”类似,都从远古时期的巫傩文化脱胎而来。